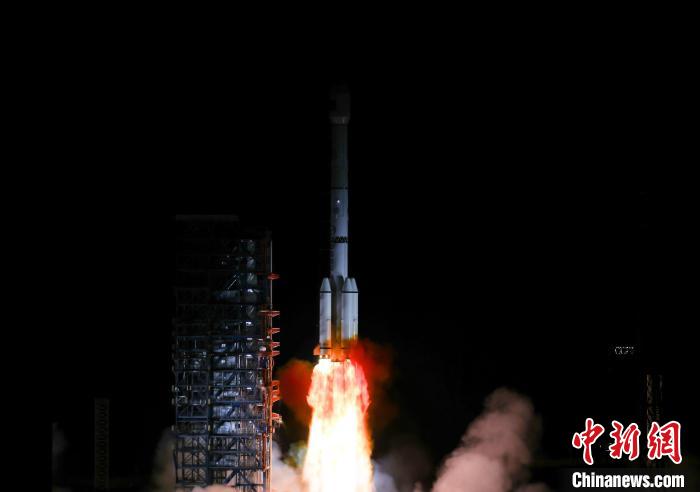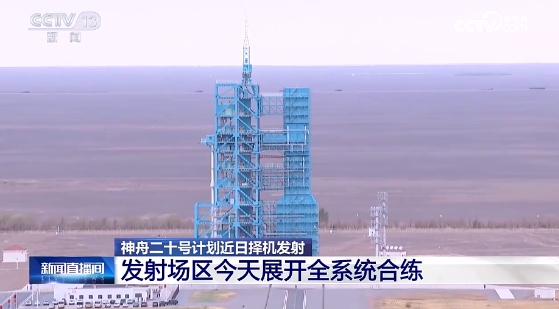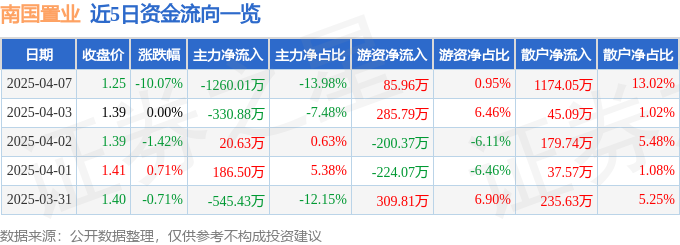门槛
连婆家在后堂前西端,檐廊比人家浅。廊下向西有个石头门洞,外面就是通向大街的藕荷弄。我记忆中,第一次穿过二房厅上街,是爷爷拉着我的手去的。一进又一进高楼,一个又一个台阶,末了还有一个高大的石头门洞。门洞的顶部和石柱上部,爬有细细碎碎的青苔。
连婆家出入的门在檐廊下,朝东。两扇高窄的木门,门槛低低的,中间部分变得薄了,外面还布满了密密匝匝的倒刺。这个门槛的对角,也是一个门槛。对角门槛朝南,横的厚木板做的,很高。门内有楼梯,门背后有一扇门,通阿红家隔壁那间。这间房子不住人,花格窗户紧闭,窗前的水门汀特别光滑漂亮。
连婆高高的,瘦瘦的,眼睛黑白分明,鼻梁高而窄。她说话爽直,走路很快,如果不去生产队,总是在两条门槛之间进进出出——楼梯下放着三脚棚、晾竿,高凳、芦席,衣服、被头,生产队分的棉花,自由地里收的菜籽,都由她一手整治。
连婆的儿子叫阿连,阿红就叫她连婆。她其实还不老,只四十出头。可能连婆家是谢姓的老住户,阿红家搬进得迟,阿红的父母教孩子如此叫了她——当时的人不比今日,喜欢人家叫自己大一辈。她也有自己的名字,叫银珠。于是,在田头我叫她银珠姆嬷,但到了二房厅后堂前,就跟了阿红叫连婆。
连婆在生产队劳动,也行动带风。她手快、脚快,因为娘家私塾里开过蒙,讲话比一般妇女有所不同。然而,当时女人讲究多子多福,生五六个是常事——养的时候辛苦,儿女长大,田地里都是帮手——而连婆只生了一个儿子阿连。可能因为这样,我总是感觉,连婆在那群妇人里,有点失落孤单。
连哥长大,连婆娶了儿媳。媳妇叫春梅,我叫她春梅姐。春梅姐从小镇南面的村庄嫁过来,屁股有点大,说话慢,走路也慢。田里的妇人说连婆:“你以为屁股大,就一定会给你生孙子了吗?”连婆却理直气壮地说:“任凭她生男生女,这又不是我能做主的。”
然而,当春梅姐有喜,连婆还是紧张得不行。她曾经拉了过路的孩子,悄悄地问,新娘子会生个儿子吗——这是东河沿婆婆最喜欢玩的把戏,但是,那个孩子已经十多岁,照道理已经不准——孩子自然说的是儿子,但是,春梅姐生的却是女儿。开了一朵金花,这是连婆当着众人说的,脸上带着笑。
然而,此后就常见连婆坐在门槛上,独自沉思——好像在听着楼上春梅姐的动静,准备随时上楼去照顾母女两个。但是,阿红却告诉我,这是连婆在做思想斗争,让我悄悄的,不要过去打扰了她。思想斗争,这是当时的时髦话,已经听烂了,阿红用在连婆身上,让我有点不懂。
不过,此后的连婆,除了去田头,带孙女,特别忙碌起来。她在后门口,那块和四房祠堂相邻的空地上,搭了一个矮草棚,养了两只猪。多养了鸡鸭,灶间关着不够,楼梯下也做了鸡舍。还把楼上箱笼理了个底朝天,凡是值钱的衣物,都拿到后街旧货商店卖了。最后,还把压箱底的几个银洋钱,也换成了现钱。
是的,她在聚集一笔钱,准备让春梅姐再生一个——那时,已经提倡只生一个好,但是,如果交上足够的款项,也可以再生一个。大的孙女刚爬得过朝南的高门槛,连婆又从什么地方,得来一个生儿子的方法,悄悄告诉了春梅姐。春梅姐也没有辜负连婆的期待,果真又有了喜。
听说,田头的妇人,又和连婆开了玩笑,说如果媳妇春梅再生一个女儿,你银珠大妈,还是如此好待她吗?连婆当然又说了男女平等的话。怕人不相信,她还当众宣布,如果再生一个孙女,请大家都吃上落地面——东河沿人的风俗,凡家里添丁养孙,亲戚邻里分一碗喜面。
然而,十月怀胎,一朝分娩,春梅姐又生了一个女儿。这天,连婆在医院里仍然强颜欢笑,回家她就坐在朝东的门槛上发呆。太阳光从石头门洞的青苔上消失了,她还不吃晚饭,依旧坐在门槛上。这天,整个后堂前都静悄悄的——大家早早吃了晚饭,各自关门睡觉了。
第二天,我从阿红那里知道,连婆这天晚上没有上楼睡觉,她在楼下的门槛上坐了一夜。还说,这是连婆的婆婆留下来的习惯,碰到不高兴的事情,不和人计较,只和自己过不去。至于连婆的婆婆碰到过什么难事,阿红说不清楚,我也没有细究。
后来,终于从生产队妇人那里知道了,连婆的婆婆,是出身名门的富家小姐,年轻寡居,独自带大儿子,娶了媳妇连婆。连婆过门不久,就生了连哥。婆婆欢喜,把当家的权柄都交给了连婆。然而,奇怪的是,连婆生了连哥以后,身子再不见有动静。
对此,连婆的婆婆没有说一句责难的话,她只是半夜三更地坐在门槛上。连婆是聪明人,她知道婆婆的心思,也不说破。后来,老人卧病在床上,连婆悉心照料,最终把她送到了山上。连婆送走了婆婆,却留下了婆婆的习惯,在碰到烦心事时,也总是坐在门槛上冥思苦想。
春梅姐坐满了月子,连婆按照约定,请生产队的妇人们来吃喜面。里屋的凳子不够,妇人们端着面碗,坐到了外面的门槛上,嘻嘻哈哈,闹得很欢。春梅姐听到了动静,也抱着孩子下楼来,一屁股坐到了朝南的门槛上。连婆忙说,这个门槛不结实,当心摔了小毛头。
不久,连婆买来木料,请来木匠师傅,把朝东朝南两道门槛都换了新的。从此,只见春梅姐带着两个女儿在门槛上玩,大的跳上跳下,小的爬进爬出。连婆一边忙碌,一边笑看着她们。有时又会数落几句,嗔怪春梅姐管教两个女儿太严。